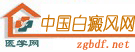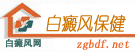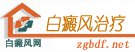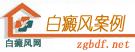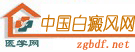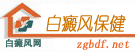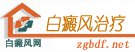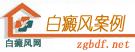|
贵刊2009年4月29日在《消解职业抱怨需要解开恶性循环》一文中提到,63.57%的中国内地医生认为当前执业环境较差或极为恶劣,的确说出了很多医生的心里话。
不久前-播出了一个医改访谈节目,北京大学卫生经济学者李玲说:“医生,原本应该是一个有着某种理想主义情结的职业。”此言让我有了一种落泪的冲动。
何为理想主义?美国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伊兹(Izzie)完成了一天的工作,精疲力竭之时,仍旧接受了一个言语不通的亚裔妇女的求助,拿上一只消毒缝合包,冲入滂沱大雨中,为一个受了伤的偷渡劳工缝合伤口。伊兹的行为说明了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而现在中国的医生中,又有多少人能像伊兹一样单纯以治病救人为理想?他们会不会担心由此可能让自己官司缠身以及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是这一诊治行为不能为自己带来任何收益。
追忆我的理想主义情结是悲壮的——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还有,在医学院里的课堂听课的时候我还有,即便是在参加工作之初也做过为身无分文的农民工清创缝合的事情。然而在真正开始了这份事业之后,它竟不知不觉的消退殆尽,取而代之的则只剩下日复一日的工作,以及工作之余的抱怨。
紧张的医患关系使我不得不在工作中分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自我保护”: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能不处理的就不处理——除非其签下“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再微小的外科操作也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解释、签字所耗费的时间往往会比手术时间更长;辅助检查“宁滥误缺”——不是我不心疼患者兜里的钱,而是怕他转过头来“咬”我一口。
前不久,笔者有幸见习了国内某知名专家出的特需门诊,见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预约好的患者按号被通知几点到达医院候诊,极大地节省了时间,避免了抱怨和冲突;宽敞的诊室,齐全的设施,很多检查都可以在诊室里完成,患者不必再穿梭于医院的各个检查室;医生会告知患者复诊时间,同时有护士加以记录,待复诊日期临近,医院会主动打电话加以提醒;诊疗结束后,当即刷院内诊疗卡结算诊疗及药品费用,省去了排队交款之苦——俨然一幅美国医师工作模式。我恍然一震,原来在中国,依然可以像美国医生一样地工作。
事后细细想来,以上和谐的医患关系有赖于以下三点因素:
一、医者精湛的技术。如果你对自己的诊断都模棱两可,又如何让患者对你深信不疑呢?为医者,如若只关心自己挣了多少钱,而不去考虑自己的技术水平如何提高,实在妄为“大夫”了。
二、医院的人性化设计和管理。电话预约有齐全的诊疗设备,当场刷卡结账为患者节约了就诊时间,优雅的环境为患者排解了心中的烦躁,独立的诊室为患者保留了隐私。但我国目前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的现实,导致上述模式难以广泛应用。试想,让一个日接诊量只有2000的医院,每天看5000个病人,无论如何的管理,也难以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
三、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特需门诊的挂号费为普通门诊的60倍,在此就诊的患者都能全力配合医生的诊治,而不是惦记着收了多少钱做了几项检查,是赔了还是赚了。这恐怕还同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体制不够完善有关。
以上三点或许是制约中国内地医生为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 瓶颈,将它们逐一突破,方能告别毫无意义的抱怨。我希望,在中国我也能和“实习生格蕾”亦或“豪斯医生”一样,一心为了解除病痛而工作。
北京 迟晨雨
|